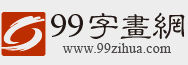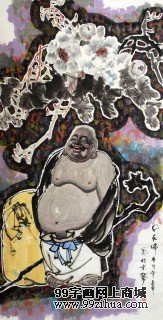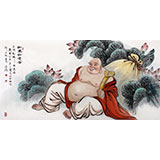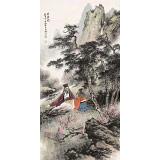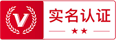西方著名美術史家貢布里希曾在其《藝術發展史》一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:“渴望獨出心裁也許不是藝術家的最高貴或最本質的要素,但是完全沒有這種要求 的藝術家卻是絕無僅有。”在這里,貢布里希強調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基本要求,就是要“獨出心裁”,否則,拾人牙慧或者一味地食古不化,都只能算是一個藝術 作品的無效“復制者”,而不可稱為“藝術家”。
李喜軍從90年代初,就開始繪畫龍門石窟佛像,時至今日已有20年。位于河南省洛陽南郊12公里處伊河兩岸的龍門石窟,是中國著名的三大石刻藝術寶庫之 一。它經過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開鑿,至今仍存有窟龕2100多個,造像10萬余尊,碑刻題記3600余品。數量之多位于中國各大石窟之首。大量的繪 畫素材得以讓李喜軍全面地掌握石窟佛像的造型、風格、背景,甚至是顧客的喜好,這對于一位畫家是莫大的幸事。
在繪畫石窟佛像的初期,李喜軍便用少年時學習的素描手法展現龍門石窟佛像莊嚴、慈愛、宏偉的形象。但是,手法和題材的新穎讓李喜軍陷入創作的盲目,這是每 一位正在創新的畫家都會面對的問題。在中國畫領域,還有一位擅于佛像創作的畫家——王玉良。李喜軍如饑似渴地臨摹、借鑒這位中國石刻佛像繪畫的先驅。但 是,王玉良先生的是把佛像從三維轉換成二維,從精雕細刻轉換成大筆寫意,體現出古拙意味。這與李喜軍最初繪畫佛像的想法正好相反,在他看來,素描是他的長 處,而龍門石窟那高大參天的佛像的垂視目光才是他所要表達的真諦。
這種思考,是要經歷過多次嘗試和反省才能得到的,而一旦得到,畫家的創造力和審美將大步提升。為此,李喜軍還開始研習雕塑藝術,為已有的素描功底,這對于他并非難事,而雕塑技能和經驗的增加,正成為他按照自己的思想繪畫石窟佛像的一柄利器。
佛教的造像、雕塑、壁畫,是信仰的追求,人類面對生命的輪回時, 即使富足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擺脫苦的煩惱。為了去苦趨吉,人們相信拯救的力量。只要有苦痛,就會有人希冀超自然的力量,李喜軍所表現的完全歸屬神圣的宗教類題材。
從繪畫上來說,藝術家不管采用繪畫還是雕塑的手段,都始終表現的是他們意象中的佛教形象符號。李喜軍的繪畫藝術,利用中國畫的筆墨材料,采用現代攝影的構 圖方式,直接面對龍門石刻遺跡,營造出了西畫般強烈的明暗、透視、立體藝術效果,既具有石刻藝術的堅實質感,又不失繪畫藝術的唯美形式。在水墨的運用過程 中又融入了素描關系的準繩,對水分的應用更是到了隨心所欲,尤其是在佛像發髻處,逐一地皴擦,讓精簡線條的佛像本身在宣紙上呈現前所未有的恢宏氣勢;還有 具象佛像的背景,李喜軍大膽地運用了“飛天”、“碑帖”、“浮云”等元素,實與虛的結合,凸顯了佛像的佛家光輝,彰顯了中華文明,更是畫家思想的全面展 現。這是對傳統藝術理念的大膽革新,也是對水墨藝術表現力的開拓與發掘。
這種把許多龍門石窟經典的佛教造像設定為大類題材,并成序列地用中國水墨與西方立體的方法表現古代佛教造像,李喜軍他嘗試了中國畫再發展的可能。
在創作的路上,他竟能恰到好處地控制墨中的水分,讓墨彩停止在物象的輪廓邊緣,猶如刀刻于山石一般,與諸多手術刀般的線條一起烘托出該佛像的精、氣、神。 這樣完全顛覆小品畫和文人畫的畫作,在當下讓人眼前一亮。迎面而來的氣勢和穩重的定力,是人們觀賞李喜軍作品后的同感。讓人無不驚嘆,面前這幅作品所具有 的完全釋放了中國畫線條的附著力和征服力。